 微信号:xxxxxxx
微信号:xxxxxxx  微信号:xxxxxxx
微信号:xxxxxxx  QQ号: x
QQ号: x 
利用春节的假期,回到了多年没有回去的老家赫甸城,看望这里的叔叔。
走进老叔的屋子,那充满屋内松树油的柴火味,充斥着房间,就是这幢房子,爷爷在这里生活了89年,直到1992年1月去世。房还是这座房,屋还是这个屋,如今虽然经过几次整修,但旧时的面貌依然可见。看着过去爷爷住过的屋子,我的视觉定格在这屋中,从中搜寻过去的痕迹。突然,我的目光停留在炕头的那个烟笸箩(东北一种盛旱烟的东西,盆状)上,那不是爷爷生前用过的吗?我问老叔,这个烟笸箩你还用吗?老叔回答还用,抽旱烟有劲习惯了,所以现在还用它。望着这个烟笸箩,爷爷生前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我家住在县城,父亲1956年就离开了赫甸城,爷爷一直在老家生活,与二叔、三叔、老叔在一起,这个家庭一直维系到1985年老叔结婚6 年后才分家,爷爷分在老叔家,房子也归了老叔,二叔、三叔出去单过去了,爷爷一直和老叔生活在一起。那时我在部队,与妻子两地生活,每年有一次探亲假,每次回来探亲都回老家看望爷爷。那时爷爷和叔叔们在一起,掌管着家庭大权,人情往份、柴米油盐都由爷爷说了算,把家治理的也很好。爷爷也是个开明老人,虽然在一些生活上还保持着一些旧时的传统,但接受新事物也快,有时接到城里我们家住,他还和我妈、我爱人打扑克,用五分硬币的过码论输赢,玩得也是好开心。爷爷一生不喝酒,就爱抽个烟,年轻时就开始卷旱烟抽,后来我每次探亲都给买点成条的卷烟,他抽着也感觉行,就说有点燎嘴,反正两样烟都抽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晚上半夜上厕所回来,不马上睡觉,卷支烟抽完了才能再睡,就这么个习惯。
我在部队每次探亲回老家看爷爷,他都非常高兴,这原因有三个方面:一是我回去都买很多吃的东西,包括爷爷年轻时没有吃过的东西;二是很多新闻(社会变革、开放)的变化,如谁家盖新房,谁家是万元户,爷爷都很感兴趣;三是与爷爷在一起回忆我小时候在爷爷家玩的事情,爷爷都会高兴像孩子。最有意思的是我念书放假时回到爷爷家,他们让我讲看过的电影,那时农村很少能看到电影,有一次全家人在一起,爷爷说:“璞子,你把你看到的战斗片讲给俺们听听!”我说“好!”我就把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讲给他们听,讲到鬼子进村时,我还把帽子下压个毛巾带上,拿个扫地笤帚当枪,嘴里哼着鬼子进村的音乐,猫腰往屋里走,把大伙逗得哈哈乐,后来这些童年的事情就成了我和爷爷在一起唠嗑的笑料,每次看爷爷,都会非常高兴地陪那么几天。
再后来,我家属随军,有了孩子,回去的时候少了,爷爷就常念叨我。最深刻的是1985年4月末那次,那会儿我回来办随军手续,顺便也回老家和爷爷告辞,爷爷念叨说:“璞子今后回来少喽!”我说:“爷爷,我有时间还会回来看你的!”我要走的时候,爷爷还亲自抄起了推碰(一种刨木板的工具),给我做了个煤铲把,说:“城里烧煤,需要煤铲,回去买个铲按上就能用!”那时爷爷已经83岁高龄了,这个煤铲直到我上楼才不用它。
“吃饭了!”老叔喊我吃饭,这时我才从回忆中缓过神来,我问老叔:“现在还经常用这个烟笸箩吗?”老叔说:“不太常用,现在生活都好了,一般就抽‘洋烟’,旱烟不怎么抽了,但这个烟笸箩还留着,也是对你爷爷的一个念想。”
1992年1月,爷爷去世,因为我在部队忙,叔叔们也没告诉我,事情过后才和我说这件事。老叔说:“你爷爷活着的时候,你们都对他很好,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了。”
如今,望着这个烟笸箩,心中五味杂陈,总会想起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光。
 提高烟草税以减少吸烟对妇女儿童健康的影响
提高烟草税以减少吸烟对妇女儿童健康的影响  广西中烟开启财务报销及付款审批无纸化时代
广西中烟开启财务报销及付款审批无纸化时代  外国香烟网上商城,外国香烟批发货到付款,免税代购正品香烟批发网站
外国香烟网上商城,外国香烟批发货到付款,免税代购正品香烟批发网站  微信卖中华烟一条120元,免税硬中华烟160一条真的能抽吗?
微信卖中华烟一条120元,免税硬中华烟160一条真的能抽吗?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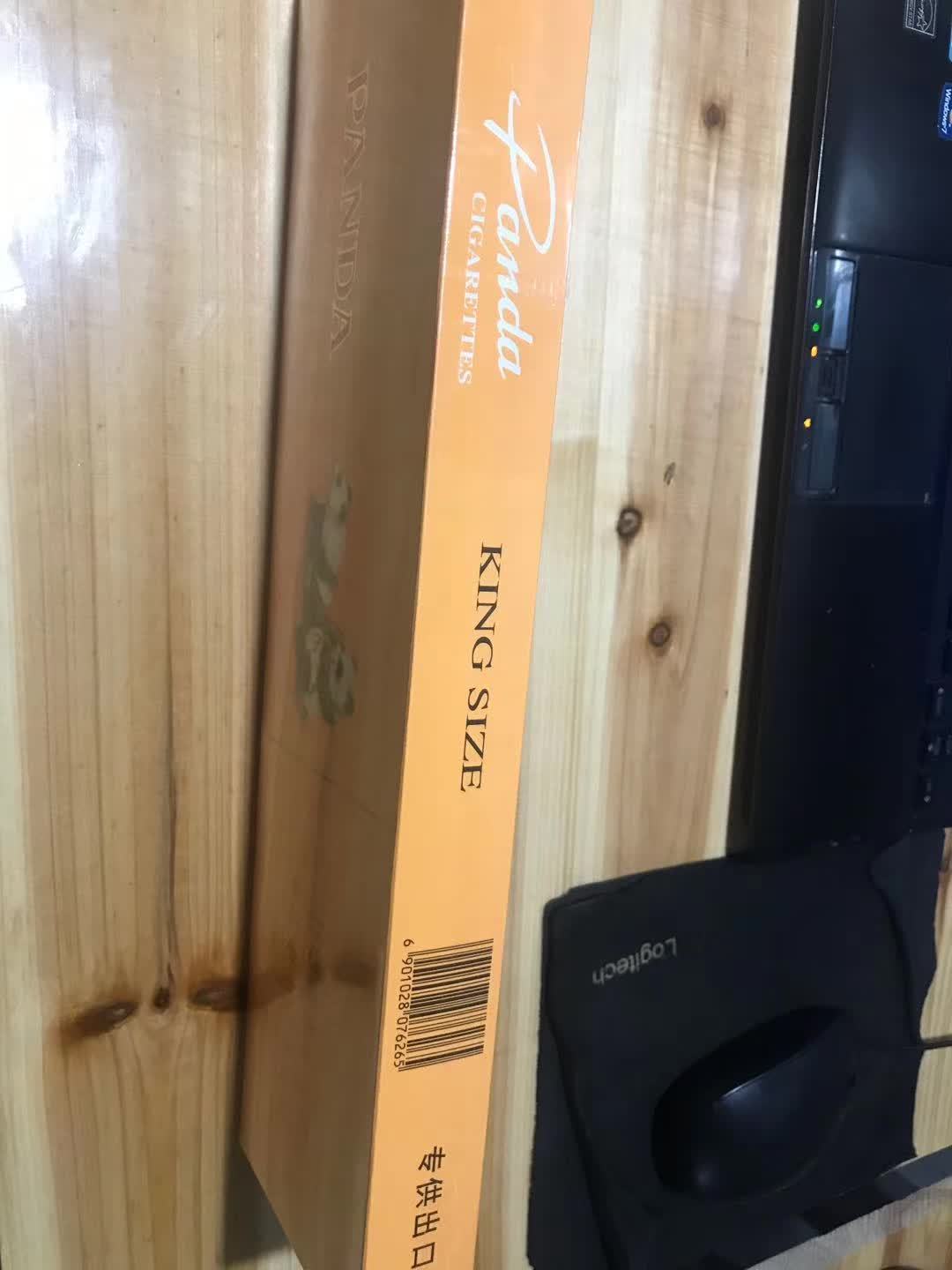 免税烟微信号|免税香烟一手货源批发厂|网上哪里有卖烟的联系方式
免税烟微信号|免税香烟一手货源批发厂|网上哪里有卖烟的联系方式  利用好“数据驱动营销”需要解决以下问题
利用好“数据驱动营销”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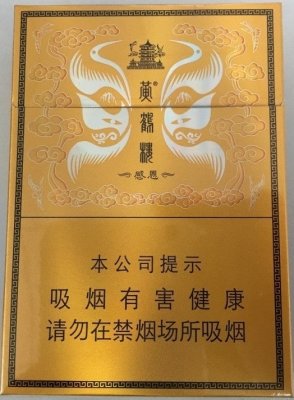 【图】黄鹤楼(硬感恩中支)香烟
【图】黄鹤楼(硬感恩中支)香烟  微信卖中华烟一条180元,加盟费多少钱?外烟货源都是从哪弄的
微信卖中华烟一条180元,加盟费多少钱?外烟货源都是从哪弄的  2023烟批发全国货到付款-香烟批发商城-香烟批发网
2023烟批发全国货到付款-香烟批发商城-香烟批发网  外烟一手货源供应商是真的,正品外烟网上代购
外烟一手货源供应商是真的,正品外烟网上代购